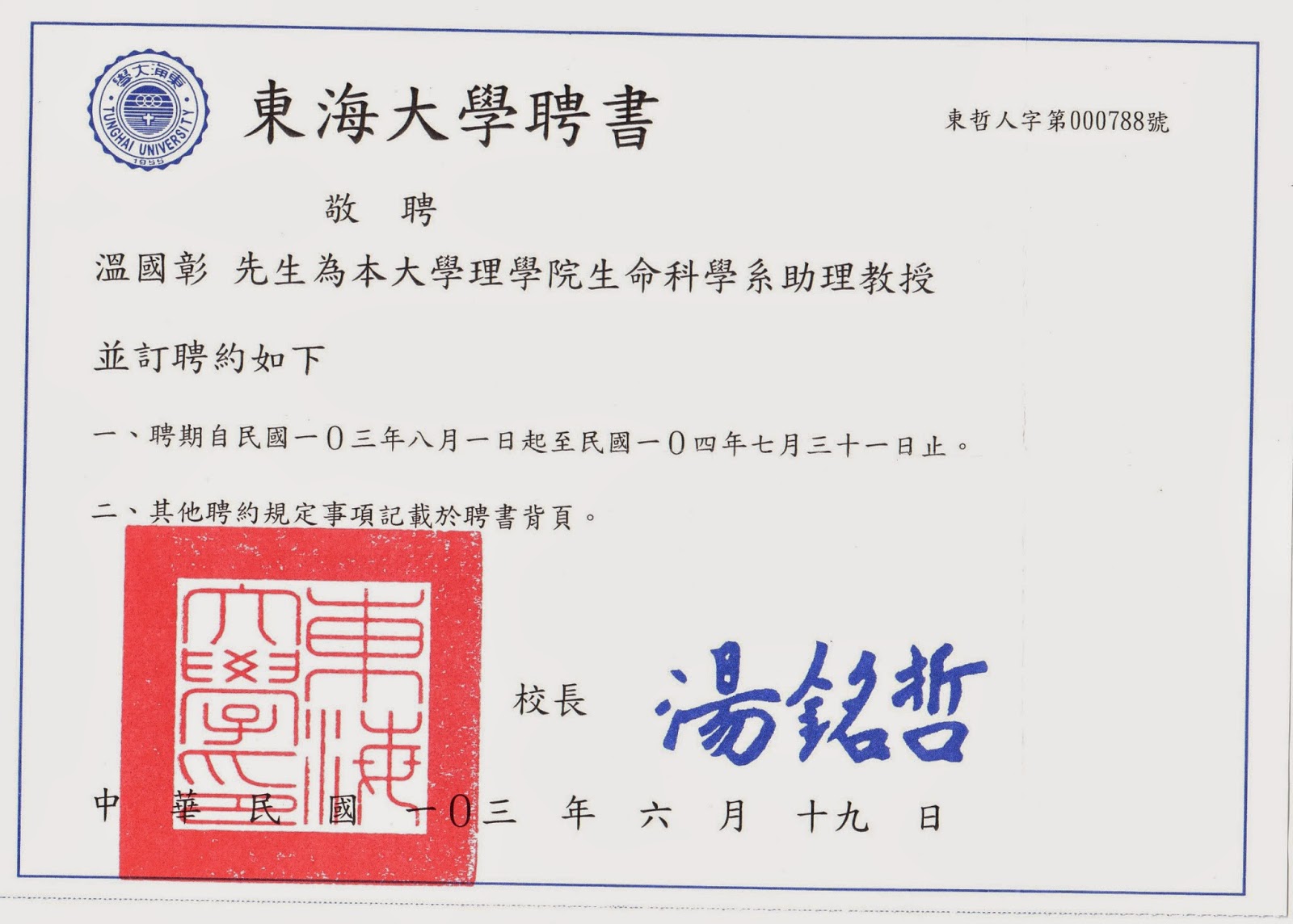前一陣子和澳洲朋友合作的文章刊登在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。文章刊登是好事,但是中間過程造成了很多的反思,經過很久也不知道怎麼去釐清這些國際合作該如何去做。
文章故事一開始是回到2017, 收到澳洲JCU朋友詢問 他們一個Global finprint的計畫 再找尋台灣夥伴。一部分對我來說利用baited video 調查,也可以解決我現階段潛水調查死角,另一方面,將這些訊息傳給認識座珊瑚礁鯊魚的老師,也沒得到太正面的回應。最終也是讓台灣會參與這個國際研究,並了解台灣礁區鯊魚的現狀。
因此就開始進行採樣公文申請、漁船安排、也讓助理跟著幾週去收相關資料,中間也和澳洲友人敘敘舊。到了2017年的Indo-Pacific Fish Conference時,另一個做鯊魚的澳洲朋友就找我聊聊這個國際合作經驗,並且寫一小段建議,來做成共同投稿的初稿。
當初在寫簡短的經驗時,除了覺得global finprint是一個好的經驗外,也把自己個人覺得台灣在國際合作上的問題寫出來。例如看到分類學者將標本館的樣本分送國際人士,換取成文章掛名。這種標本掮客的方式,讓我以為回到一百年前。也分享看到珊瑚研究人員,大量引進西方學者,利用國家資源的魚缸場域進行各類型實驗,一樣是提供場域換掛名。也還有透過不同關係,拉近西方研究船,長期進行調查一些本來台灣就有在進行的研究。差別只是台灣方合作者並沒有相關能力,只是有海外關係,所以透過合作方式讓外國學者在台灣調查。
雖然後來這些文字,好像因為太像抱怨而不是和正面表列在這個文章中,被輕描淡寫的帶過,但是因為也提供一些貢獻,被列成這文章的共同作者
。更諷刺的是那個來台的珊瑚研究船的主持人,竟然也是共同作者!(還列在我名字旁邊) 。真好奇這位研究船主持人對於來台研究的看法,是寫在哪一段!
話說”when you point a finger there are three fingers pointing back at you”,這篇訪問學者討論文章,我只是抱怨一下,就變成共同作者,跟送樣本給外國人換掛名,有什麼差別?最近也是同樣在進行豆丁海馬研究時,因為台灣缺乏相關技術(micro CT scan和不容易取樣小型樣本的分生技術),加上進台灣標本館又會回到標本掮客的循環上,所以改連絡澳洲博物館朋友。最後結論也是要把樣本送出去。這樣我和標本掮客又有什麼差別?
目前與德國ZMT合作,也是共同指導研究生,來台灣延續兩邊當初進行休閒餵魚影響的研究。當初也是大學生的專題,但是沒有人願意留下來繼續做研究,所以一個適合的題目只能放給外國人做。這樣我跟邀請研究船來台,或是邀請國外學者來用台灣大水缸的這些研究人員,又有什麼差別?
過去曾和中研院珊瑚礁研究老師聊天,這老師是一直很努力做出台灣好的研究,讓國外研究團隊找他合作,而非像是提供場地或是樣本的合作方式。這位老師也一直很努力訓練培養台灣學生,想讓台灣的珊瑚礁研究能站上國際。日前也看到他們的國際合作上了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,也替他們高興。雖然另一個引進國外研究船的台灣研究人員也在其中。至少希望台灣是合作單位,而非資料提供單位而已。
在有發表壓力的學術圈,要提升自己進行國際合作,又不想要變成單純掛名的人,真的好像不容易拿捏尺度。一不小心,就跑到dark side of force,變成自己不喜歡的人。套用另一位朋友的說法,不想要”擁洋自重”,但是一不小心,自己也可能變成這個”洋”,跑去其他國家請他們提供資料或樣本。只能時時刻刻提醒自己,不管是當visiting scholar或是host,都要平等的交流,並且進行互惠的國際合作研究。